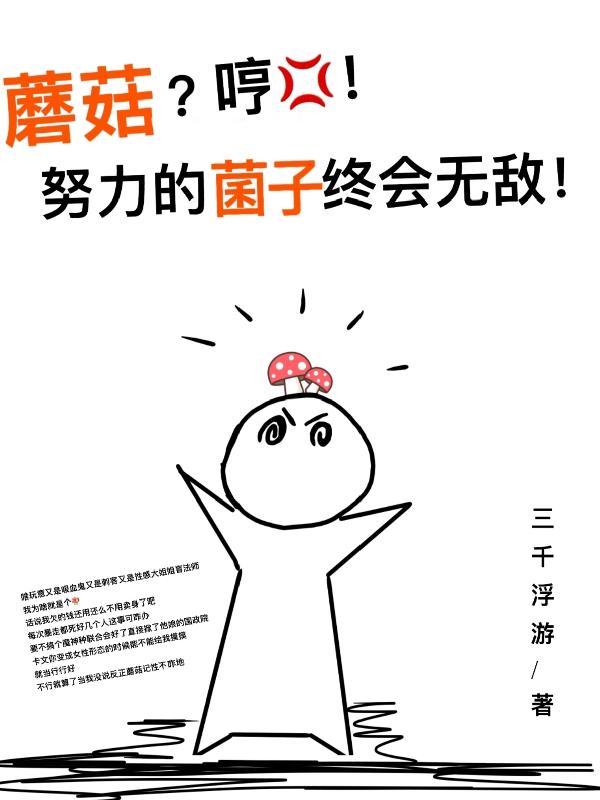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剑如夕 > 第二百一十六回 借刀救孙(第1页)
第二百一十六回 借刀救孙(第1页)
坐不多时,门外人声喧嚷,几个红衣女子押着一个男子进屋来。只见那男子散开了辫子,蓬头垢面,被块手帕堵了嘴,呜呜叫唤,正是徐濯埃。
屋里几人见了,便要上前殴打,苏见黎忙道:“且慢!”说着,走到徐濯埃面前,瞧了他几眼,道:“这厮想捉我与顾大哥回京,固然可恶,看在他击杀薄仁,终究是救我一命,先饶过他罢。”
刘呈祥叫道:“苏小姐!我义和团弟兄被他家府兵杀死许多,不斩此人之首,弟兄们岂不是枉死?”
苏见黎道:“刘首领差了!你不晓得这人身份。他爹徐承煜和祖父徐桐,都是当朝太后器重的大臣。若杀死他,徐家必然拼命报仇,到时候不好收拾。依我看来,这个活的徐濯埃,却比死的徐濯埃,还有用。”
刘呈祥不解,正待回言,顾旸在床上接话道:“阿黎说得是。我虽也有心除了这忘恩负义之徒,但若把他当做把柄,牵制徐家,好处更多哩。况且咱们方才把他府兵一杀而尽,弟兄们的仇,原也算报了。”
刘呈祥听说,转颜为喜,道:“顾师兄说得也是!”
当下两边计议已定,便把徐濯埃锁在怀庆药栈的马厩里,义和团众各自离去。
徐承煜在京师久等徐濯埃不至,心已生疑,又不见半个人回来报信,便派府里下人骑了马,去天津打探。
下人数日而回,道说公子被擒,府兵尽歼。
徐承煜震惊之下,当即晕倒,半晌方苏,咬牙道:“与我点兵,救回濯埃!”
下人苦着脸道:“老爷为着公子此番事成,特意把全府兵力都交给了公子,如今哪里还有兵马?”
徐承煜一听,心中如碎,登时捂住胸口坐下,干咳起来。
“不教你去招惹那帮子草莽,你偏要去,还让儿子去!”屏风之后转过徐夫人来,捏着手帕,声泪俱下。
徐承煜被她责怪,更加心烦意乱,本要叱她下去,又想原为自己的不是,只得捶桌顿足,不住长叹。
徐夫人泣叫道:“你身为男子大丈夫,儿子陷在他城,就没一点主意么?”
徐承煜烦躁,把桌子一拍,哭声戛然而止。
徐承煜便叫下人备马,亲自跑去宫中,告知父亲徐桐,徐桐虽然悲骇,终是老臣,见惯风波,急忙求见慈禧太后,请太后拨些兵马前往援救。
徐桐跪在地上,老泪纵横,哆哆嗦嗦讲了多时,太后却始终沉默。
徐桐见势不对,心想说多了,慌收了口,连连磕头道:“孙儿落难,微臣寸心如割,情……情难自已,还求太后恕罪!”
“徐师傅。”太后悠悠地道,“你糊涂啊!”
徐桐听太后有责怪之意,更是把一颗老心提到了嗓子眼,趴在地上发颤,只不敢抬头。
“这摞子奏折,都快高过咱家了。”太后道,“聂士成说,一伙洋人士兵登了陆,约莫三四百人。怕是要对咱不利。”
徐桐道:“微臣想来,聂提督……聂提督,有时就有些太杞人忧天啦。”
“大胆!”太后叱一声,把指骨在椅子扶手上一敲。徐桐慌忙趴得更紧些。
“对咱不利那话,原是我说的。”太后道,“聂提督汗马功劳,何时有负大清来着?”
徐桐听得汗流浃背,只是颤声念道:“微臣……微臣有罪!太后恕罪!没有太后洪福相佑,没有大清的江山社稷,哪里有微臣?微……微臣家小,便是为国家而死,原也是光耀先祖,不负朝廷!”
“你们呐,虽是文臣,国事当前,也当为我分心才是啊。”太后扶着额,闭了双眼,“咱家累了。下去罢。”
“微微……微臣告退。”
徐桐战战兢兢,退出宫去,徐承煜本来欢颜相迎,见了老父面色煞白,当即把舌头打了几个结。
徐桐道:“如今洋人往北京增兵,似有……起战之心。太后明里暗里,点拨于我,赴身国事。”
徐承煜急道:“那濯埃呢?濯埃就不管了?”
“楠士,你如今……如今岁数也不小了,一二品的官阶,莫再事事仰仗着爹。”徐桐道,“濯埃被他们捉去,若要杀时,早已杀了。……所以不杀,正是有意挟持你我。大敌当前,咱爷俩……便莫去烦扰太后了。”
“话虽如此,濯埃一人陷在那里,儿子如何放心得下?”徐承煜沉吟道,“爹,我去雇伙杀手。”
“糊涂!”徐桐哼了一声,“‘走一步,看三步。’为父是白教你了。如今……如今你也是六十岁的人了,如何还跟孩子一般意气?你又不是不知,那姓顾的小子……本事高强。莫说一伙杀手,便是百余兵马,又能稳胜过他么?”
徐承煜道:“依爹之见,该当如何?”
徐桐道:“那顾旸有意挟持于我,濯埃一时之间,定无性命之忧。太后……不是说洋人有意来犯么?如今国家以内,拳匪之众,诛不胜诛,屠杀洋人。大清与洋人开战,只差火上一把油。到那时……到那时你我父子,便在朝中一力主战。兵戈一旦起于京津,咱们借大清的雄兵,救出濯埃,……岂非轻而易举?你我父子,再痛击洋人,还能立些战功哩。”
“爹,您不愧是我亲爹!果然智谋无边!”徐承煜听得大喜,连连给徐桐捶背。
“当年曹孟德能借刀杀尔衡,为父如何不能来一个借刀救孙儿?”
“正是,正是!爹,您这边请……”
喜欢剑如夕()剑如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