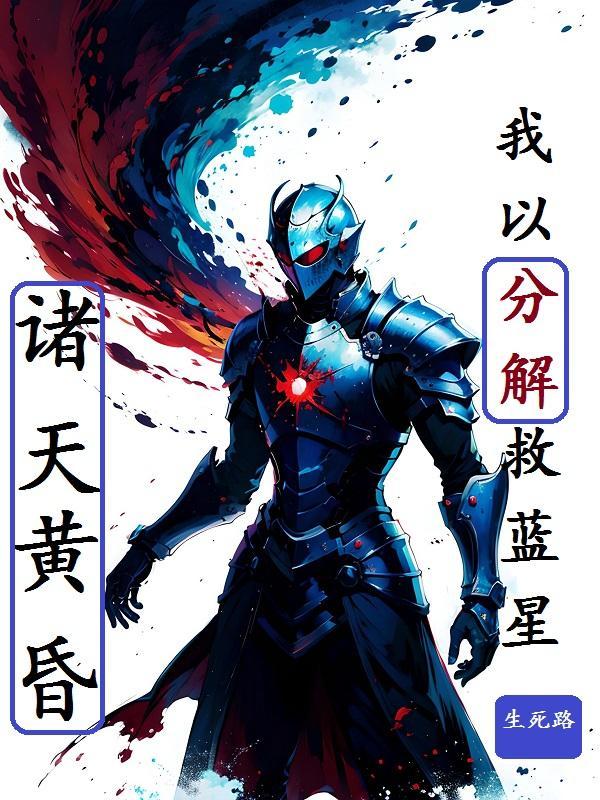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芙蓉帐暖,清冷小叔不经撩 > 第110章 千丝万缕的羁绊赐婚(第3页)
第110章 千丝万缕的羁绊赐婚(第3页)
昨夜疾风骤雨,将院内花草摧残得不像样,谢希暮爱惜花花草草,驻足看了一会儿,才随着下人入书房。
老人比起昨夜看起来老了不止十岁。
往日挺得笔直的脊梁骨,好似受了和谢识琅一样的仗打,如苍老垂柳弯了下来。
“不向我行礼?”
谢端远缓缓抬起眼来,女子站在他面前,却无动于衷。
“恨我?”
谢希暮熬了一整夜,嗓子也跟着有些哑:“应该是老族长恨我吧。”
谢端远冷笑了声:“我是恨你。”
恨这个女人让他的孙儿走上歧路,执迷不悟。
恨她让清明一世的谢家背上污名。
可恨来恨去,他又不知该恨谁了。
正如谢识琅所说。
谢希暮又做错了什么呢?
“希儿。”
老人从未像如今这般苍老无力,“你是一步步看着他走到今日的。”
谢希暮深吸一口气,“时至今日,老族长还是不愿意让他同我在一起。”
谢端远没有承认,而是直直看着她,“谢家养你到了如今,若非我们,若非十郎,你活得到今日吗?”
她似是笑了,可眸底却有泪光。
“希儿,你很聪明,你该明白的,他同你提亲,这是出于他的责任心,和这些年你们相伴的情谊。”
“可你们之间没有男女之情啊,就算成了婚,他会像对心爱的女人一样待你吗?”
谢端远老眼拧在了一起,苦口婆心,“夫妇之间没有感情,时日久了,亲人不像亲人,眷侣不像眷侣,平生怨怼,不得安生。”
“若是没有你,他会娶一个心爱的姑娘,哪怕门不当户不对,至少他不用背负天下人的骂名,希儿,你该清楚的,十郎这般好,他该拥有更快活的日子。”
老人颤颤巍巍起身,走到谢希暮跟前,塌了肩,佝偻着背,老态龙钟。
“希儿,你清楚这其中利害的,难道舍得看他为了你背负上这些骂名,痛苦一辈子吗?你这究竟是爱他,还是害他?”
屋内鸦鹊无声,寂若死灰,犹似广阔无垠的海面,浪静风恬。
小窗外徘徊着南飞的鸟雀,停在树梢不多时,终究认清了自己的位置,重新起飞。
整整五日,谢希暮一直守在明理院内,盯着手底下人熬药,每日晨起给谢识琅服药,再扶人躺下去,给他打水擦身子,再更换里衣。
谢识琅始终没有醒过来,其实谢希暮清楚,谢端远让人动手是收了力的。
这板子上的功夫,说强短短三十仗便能要人命,谢识琅受了八十板,虽然如今还昏睡着,但大夫说了,骨头没有大事,不会残废。
他如今昏着,但不能不吃东西。
谢希暮每日给他服药后,会去小厨房熬一锅米糊,就像喂药一样慢慢喂下去。
她没有再回朝暮院,而是让阿顺在外屋支了个小榻,方便进出照顾谢识琅。
到了第五日,谢识琅身上彻底不烧了,大夫查看过后,说伤口已经结痂,很快便能转醒,等再好好休养一段时日,便能下床走动了。
谢希暮亲自送大夫出了门,才回了谢识琅的屋子。
人还睡着,她坐在榻边,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。
就像是她幼时,他办完差事后回家,总得看一看她。
“原谅我的胆怯。”
她轻轻抚上他的脸,“我不敢等你醒来再走,我怕我会舍不得。”
“承蒙你多年照顾,我深知不能再拖累你,老族长说得对,我这是在害你。”
男子面庞温凉,她俯身靠近,轻轻用脸蹭了蹭他的脸。
她用极柔的语气在他耳边说:“白云苍狗,天各一方,我心念你,永世不忘。”
*
崔氏夫妇收拾的手脚很快,不过两日,便整装起程,阿顺在京城待了十多年,说走就走,还真是有些不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