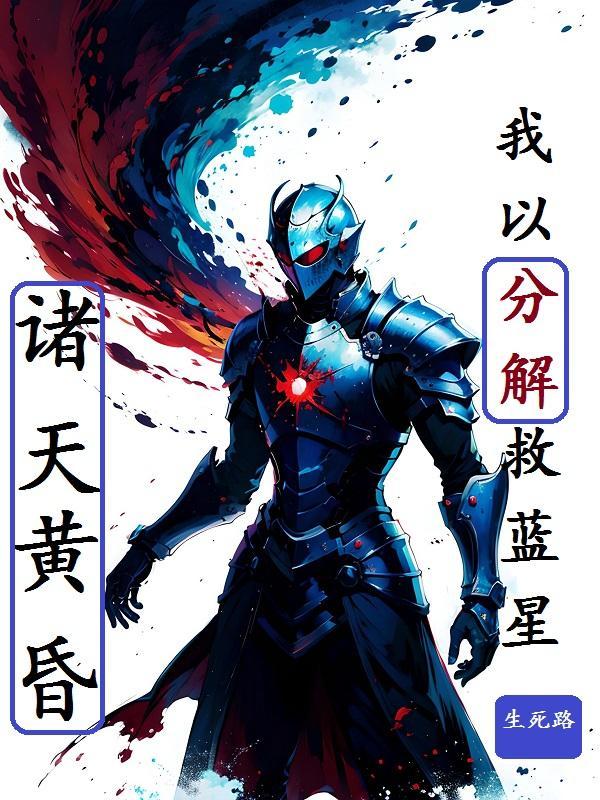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芙蓉帐暖,清冷小叔不经撩 > 第110章 千丝万缕的羁绊赐婚(第2页)
第110章 千丝万缕的羁绊赐婚(第2页)
男子无声将后背碎裂的破布撕下来,含在唇间,吃力地趴伏下去。
头顶上,烛火晃荡,映在高高垒起的牌位上,恍若一双双黑沉的眼,紧紧盯着受打的谢识琅。
便好似数夜里,父兄入梦对他的指责,此刻,他们再度降临,来见证他的决心。
身后仗打声还在继续,谢识琅却感受不到疼痛,只听忽近忽远的一道崩溃决堤声,泥流滚落,高山塌方。
天崩地裂间,他眼前浮现出女子动人笑靥。
高高悬挂,名为伦理世俗的防线由此彻底断裂,是释然。
眼下就算是万丈深渊,她在前方,他也要跳。
最后一仗落下。
随之老人背脊骤然垮下来,嘴里喷出一口鲜血。
阿梁和阿蟒扑过来,想将人扶起来,可谢识琅伤得太重,根本起不来身,只能重新趴在地上。
“谢识琅,值得吗?”
老人家捂着胸口,满目沉痛。
年轻男子起不了身,只能抬起眼,这样一眼,让谢端远忽然想起谢识琅在幼时,也曾这样抬起眼仰视他,稚嫩幼子,丧了父兄依靠,那样无助恐慌,好像整个世间都抛弃了他。
可眼下,他却抛弃了所有,独独要一个姑娘,
“八十大板,换我和她的前程。”
谢识琅嗓音从未如此虚弱,似是艰难笑了声:“太值了。”
……
祠堂行刑之时。
郝长安带着谢乐芙登崔家报信,女子的哭喊声惊动了整个宅子,谢希暮急忙从院子里赶过来,只见谢乐芙挣脱郝长安的搀扶,扑进了谢希暮怀里,泣不成声。
“大姐姐,二叔他被老族长责打,你快去救救他吧。”
谢希暮惊了,没想到谢端远会这么狠,飞快赶到丞相府,祠堂内只剩下一片狼藉,血渍斑斑。
她心里咯噔了一下,转头跑去明理院,主屋内灯火通明,踏入门槛汹涌扑过来一层浓郁的血腥味和药气。
阿梁将熬好的药给榻上人灌了下去。
谢希暮眼瞧着白日里还好好的男子,此刻眉目紧闭,丝凌乱,脸上乃至于唇上没有丝毫血色,趴在榻上,上半身未着衣裳,被纱布包裹住的后背还不停往外渗血,未被纱布裹住的皮肤也全都是近乎黑的瘀紫。
被褥上粘黏了一滩血渍,即使阿梁给谢识琅灌下药,却怎么也灌不进去。
谢希暮浑身抖,不敢置信地瘫坐在榻边,第一次全身提不起力气,艰难地爬到榻上,手指颤颤巍巍去探他的鼻息。
还有气儿。
她吓得大汗淋漓,说出口就成了抽泣:“小叔叔、小叔叔。”
阿蟒将药罐子放在一旁,扶住谢希暮。
阿梁安抚:“方才大夫来过了,八十板虽重,但好在主子平日里身子结实,性命无忧,只是伤口感染,又生高热,属下喂药怎么都喂不进去。”
八十大板。
寻常人三十板便能打得皮肉脱落。
谢识琅竟然生生挨了八十板。
听到这个处置,谢希暮整颗心都好似掉进了冰窟里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将面上的泪痕胡乱擦掉,紧接着接过阿蟒手里的药罐,“我来给他喂。”
倒也像是冥冥中注定好的。
药罐子在阿梁和阿蟒手中不起作用,由谢希暮喂药,男子竟然真的全喝了下去。
谢希暮喂完药,又打来水,替谢识琅不停擦拭身子,反反复复的,生生熬到了后半夜,他身上的烧热才勉强平息了一点。
女子一夜未睡,阿梁多次劝说都无果,只能瞧着谢希暮一直坐在他榻边伺候。
到了辰时,也不知道谢端远从哪里得来的消息,知晓谢希暮来了,命人来请谢希暮去说话。
阿梁起先是拦着,不准老族长身边人带谢希暮走。
纠缠了许久,场面也闹得难堪。
阿蟒都要拔剑相对。
被谢希暮拦了下来,对二人宽慰了两句,便随着老族长的人去了别院书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