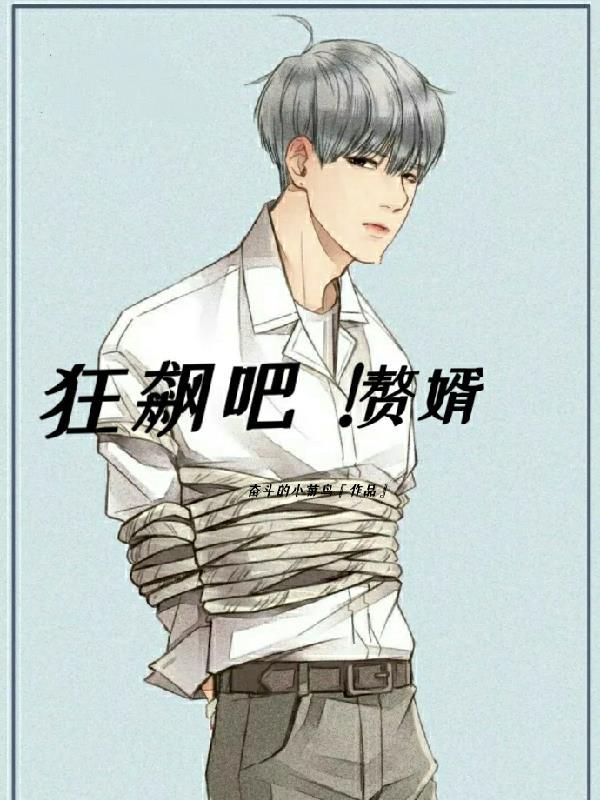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被落难皇子讹上后,我独享娇宠 > 第96章 狭路相逢(第1页)
第96章 狭路相逢(第1页)
崔康时手掀着车幔,望着后方早没了马车影踪的山道,轻应:“满意!”
一口寒气呼出后,他问:“可有伤到人?”
这辆马车宽敞,同坐车内的还有四位黑衣府卫,闻听他问,便七嘴八舌接起话来。
“没伤到她,倒是我这颈子被她抓得血淋淋的。”
“那小娘子委实泼横,我们三人险些按不住。”
“也不知是个什么性子,我们六个人她愣是不怕,又打又骂的。”
崔康时放下车幔,唇边弯出抹浅笑,低叹:“宋卿月,委屈你了!”
被抓伤的府卫闻听便绿了脸,好像他才是受委屈之人。
钟裕便也笑了。
“钟伯,你回去后,去浮香辉月定三万两银子的香药。”
“三万两……”钟裕微讶,“会否让宋娘子觉得出手太阔,增生她之贪念?”
“多借几家名号去下订单,两个月内定完,别透露是我。”崔康时疲惫阖上双目,“……她想挣干净钱!年关将近,就当送她的贺年礼。”
钟裕更讶:“不透露主君,宋娘子又怎会感激主君?”
崔康时吐字缓缓:“无需她感激,也无需她知道,她开心就好!”
之所以如此折腾,他一是想看宋卿月时是否肯临危救护珍娘?二是想看宋卿月将钱看得有多重,会否因惜财而舍弃珍娘?
钟离向他估过浮月辉月的营收,开业短短时日,要价三千两于宋卿月而言,非是小钱!
今见宋卿月做派,区区三万两,远不足酬他的感激之情,更不足表他心底的欣喜之意。
他是个商人……
不看准、不摸透,决不会下注,更不会做亏本的买卖!
钟裕轻一颔。
……
马车内,宋卿月搂着珍娘指向窗外的夜穹。
“诺,那粒星呢,叫太白金星,听说那星星上住着位老神仙,老神仙白胡子长长……”
马车刚将拐过一道弯,忽听前方响起一阵如雷般疾来的马蹄声。
宋卿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,霍地就掀开了帘子朝前方望出,全神戒备。
暮色里看不清来人模样,但见道上驰来仅一匹马,其上坐着一个人,遂放下心来。
只是待马近了,她一眼认出马上人,大喊出声:“宋玉书?表哥?”
宋卿月未尝见过宋玉书骑马的样子。
眼下的宋玉书一身玄色短打劲装,背插两把锋利的铡药刀,腰间还挂着一把短木棍。
他纵马越过马车后,闻听她唤,急急将马匹勒停,一个翻身下马,扑到车窗前。
他髻散乱,满脸惊惧地望入车窗,一见车内果真是宋卿月,凤目里立时泛起了雾气,抖着嘴唇高声:“卿月,你可安好?”
大惊大恐之后,宋卿月一见到亲人才鼻子一酸。
这大好的节庆,无风无雪,偏偏流日不利,什么破事都让她遇上,累得她险些跑丢三魂,吓飞七魄。
抽了抽鼻子,她哽咽道:“没事!吓着你了吧?”
随后,宋玉书骑马伴行马车右侧,听她细细将事情经由讲了。
宋玉书眉头深蹙道:“若只你一人经历此事,我定觉你是被山鬼勾了魂,或被梦魇住了,做了一回离奇的恶梦。”
是啊!哪有劫匪眼看钱财就要到手,却放了人,不见了影踪?
走了没多远,但听远方马蹄声与叫嚷声如潮水般响起。
遥遥一看,远方涌来无数骑着马,坐着牛车,或跟在后面乱汪汪急跑的人。他们手中举着的火把照亮了山道,映红了半片天。
宋卿月忙将珍娘紧紧搂于怀中,只道是那批贼匪又来拦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