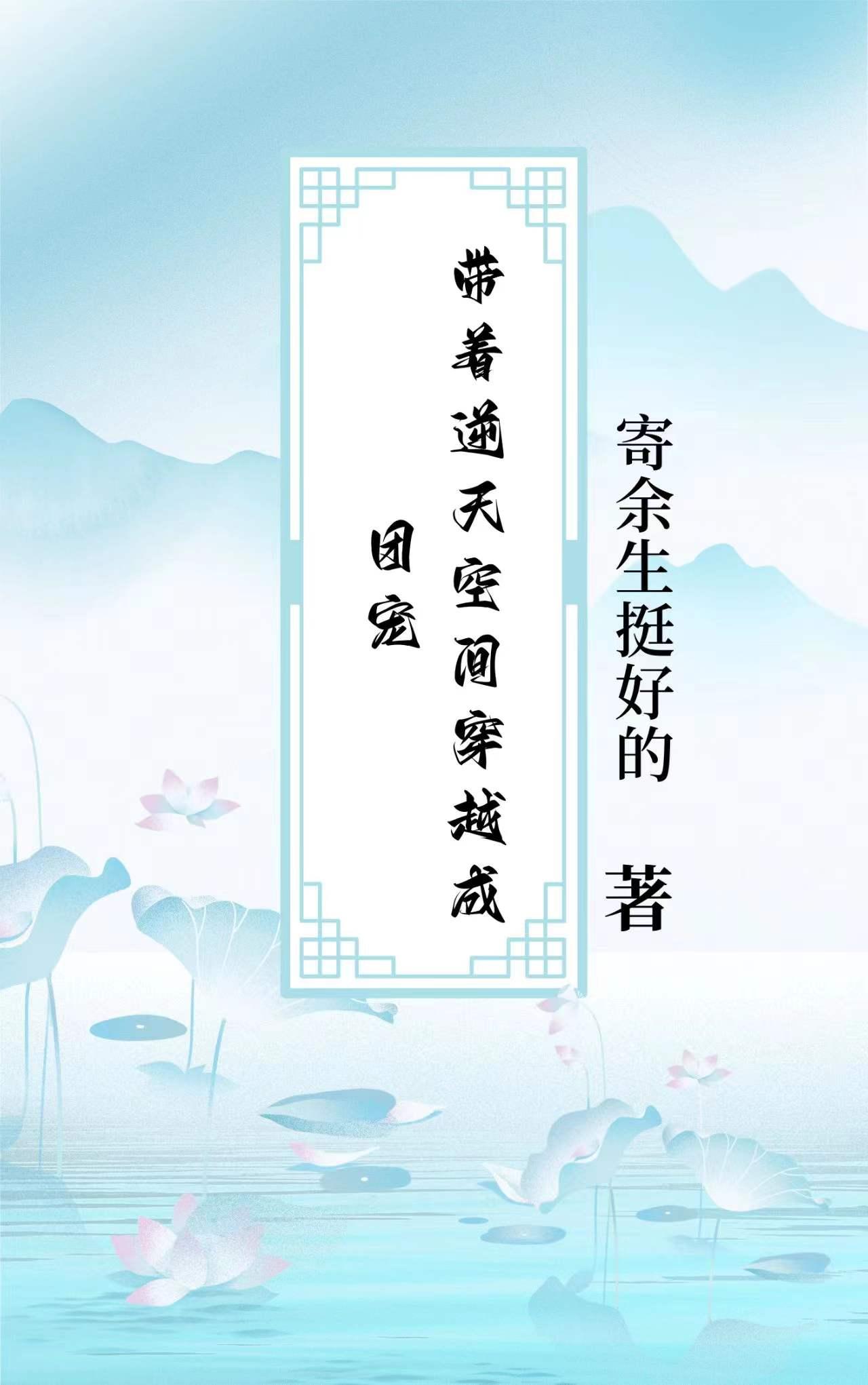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剑如夕 > 第二十二回 青花瓷碗(第1页)
第二十二回 青花瓷碗(第1页)
“顾大哥,你有所不知,我那娘亲……她在我爹爹最后一年赶考时,与那知县勾搭成奸,抛下了我和爹。她不配为人母。”苏见黎道。
顾旸听了大惊,颤声道:“为什么?”
苏见黎淡淡地道:“没有为什么。我只知道她无情无义,我恨她。”
顾旸道:“你娘说不定也有甚么苦衷。”
苏见黎听得,瞪了他一眼,道:“她负了我爹,与别的男人成奸,她能有甚么苦衷?”
顾旸道:“她是跟谁成奸?”
苏见黎咬着牙根道:“正是那昆山知县冷观,这名字我绝不会忘记。”
顾旸一愣,正要问这昆山在何处,苏见黎便道:“这昆山县隶属江苏省苏州府。”
顾旸沉吟道:“你们是江苏人氏?难怪你们姓苏。”
“哎呀!”苏见黎轻轻打了他肚子一拳,嗔道,“这姓苏跟江苏又有啥关系嘛!”
顾旸摸摸肚子,笑道:“我傻了。你且说说当年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苏见黎道:“一言难尽。说起来,我苏家祖上本是山东一耕织人家,只是百年之前,门里有人考中进士,一跃而为京津望族。数代之后,子弟荒侈,外加政敌构陷,故而被朝廷查抄,家道中落,爷爷忧愤而死。我们一家三口拖着奶奶、姥爷、姥姥三个老人,辗转流落至苏州府昆山县安平村为民。爹爹曾说,爷爷临死之前,握住他手,嘱他定要把苏门复兴。”
“故而爹爹倾心于科举,一意定要考上。赶考九年不中,九年之间总是离多归少,每年只在大年三十回家来,住上十数日便走,这十数日之间,却又每日被那些个家长里短闹得鸡飞狗跳,苦不堪言。”
顾旸道:“却是为些甚么争吵?”
苏见黎道:“我那时还小,记不太清,只记得最后那年爹爹带回来只青花瓷碗,送与我娘,被她失手摔了。我趴在里屋墙边,见爹爹只是责怪了一句,我娘竟大吵大闹起来,一连摔了十几只碗。”
“那时爹爹便道:‘只是说你一句,何必无理取闹,动如此大肝火?’”
“娘叫道:‘你一去九年,讨不得个一官半职,直连累得我几口老弱,在这异乡受尽人欺。摔你个碗又怎么?也值得怪罪?’”
“爹道:‘我给人家教书,半年才买得这只碗来,你顷刻摔了,我却说不得?’”
“娘便道:‘你正是说不得。你在外面出风头,可知我在这家里受尽多少罪么?’”
“爹便怒道:‘你道我在外面便风光么?一年里挣几文破钱,走南去北,打点结交名流,你道我便容易么?我却为的甚么?还不是为这个家?我漂泊于那市井街头,忍饥受冻时,又有谁记挂着我来?’”
“娘道:‘你这九年,却给这个家带来些甚么?你可曾金榜高中了?’”
“爹便道:‘不曾。这之间的委曲,你也应知道。’”
“娘道:‘那又如何?你不如老老实实回乡来种地,或是做些生意,莫痴想着甚么高官厚禄。这些话我每年都说,早说得倦了。’”
“爹怒道:‘爹临死之时,你也曾在身旁,这如何便是痴想了?’”
“娘道:‘你两次三番中了,便不是痴想,九年不中,换别人家媳妇,有你这等丈夫,早些年就跑了,只有我这般老实的,跟你受苦!’”
“爹大怒,站起身来,往娘脸上打了一掌。娘捂着脸大哭大叫,似疯似癫,道:‘你打我,你打我!你不让我说,我偏说!这些年来,我跟着你过得是甚么日子?你把家一抛,倒是利索,你却闯出个名堂来哇?舍下我们这孤儿寡母的,三个老人也一个接一个送终了,我做媳妇的该受的苦都受了!要不是还有这个丫头,我早一头碰死了……你要打我们娘俩,就打罢!我先把这丫头掐死,你打我罢!’我听得赶忙跑到床底去了。”
“爹听了却懊悔,饮了一碗酒,那碗又被娘摔了。爹便出门去天井望了一阵月亮,娘坐在堂屋哭。爹回来时给娘赔了一夜不是,并许诺说这一年必定考上,若再考不上,便回来种田、做生意,又或是允她改嫁。”
苏见黎说得这一大篇,演得栩栩如生,顾旸虽只见过苏父,未见过她娘其人,被她这大呼小叫一顿演,便如看见了她爹娘二人争吵的场景似的。
听她说到此处,顾旸便喜道:“苏大人最后一年却考上了呀!你娘不用改嫁了。”
苏见黎道:“本来是应当如此。第二日,来了位姓徐的官大人投宿,还带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男孩。我爹既有意入仕,必然用心相待。那徐大人自称是朝廷来的鸿胪寺少卿,松江府上海县人氏,逢年回乡探亲,不料路遇洪水,便绕行至我们村里投宿。”
顾旸晕乎乎地道:“莫非是此人祸害了你娘?”
苏见黎摇头道:“顾大哥,你且听我说。这日到了傍晚,又来了一个官员投宿,你道他是谁?便是我们那昆山县知县,冷观。”
顾旸惊愕道:“是他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