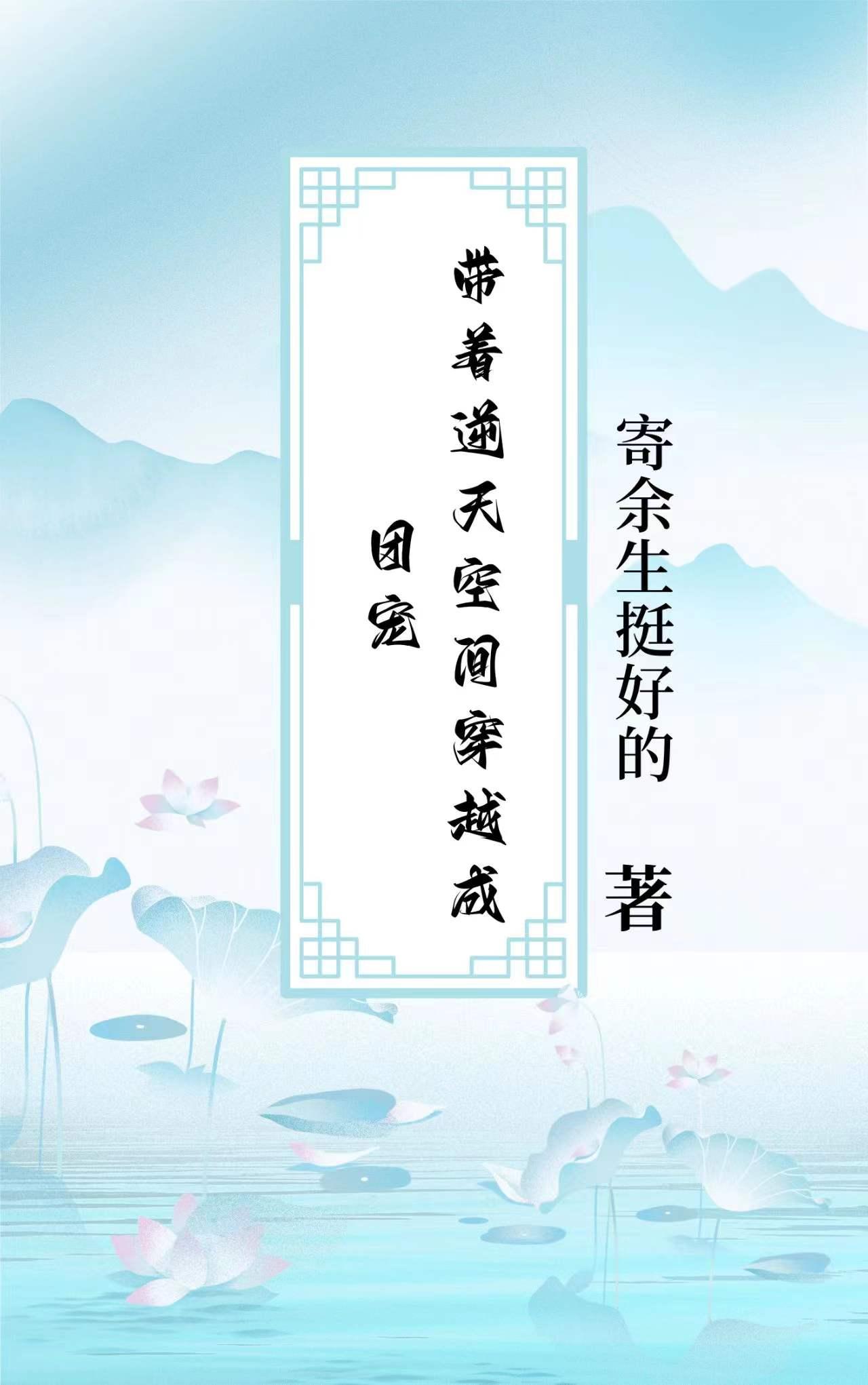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极恶仙人传 > 第51章 又遇(第1页)
第51章 又遇(第1页)
文安连忙双手接过来,兴奋而又欣喜地道“谢谢大叔,大叔,这部书是不是记载了所有的药材呢?”
张九龄闻言微微一怔,继而失笑道“傻小子,世间药物多不胜数,区区一部书怎么可能尽数收录,这部书记录的也只是常见药物罢了。”
文安红着脸道“让大叔见笑了,那大叔,你这里有哪种记录比较全面的书吗?”
张九龄有些奇怪地问“你问这个做什么?”
文安挠挠头道“我看你这里有这么多书就有些好奇,也想知道有没有那种记录比较全面的药书。”他其实想找找有没有一部书记载着龙涎玉芝,他想知道这个差点害死他的东西究竟有多神奇。神农本草经里他是没有现,就是找到了龙涎草和一些灵芝类的药物,和龙涎玉芝不沾边。
张九龄不知道他的心思,就以为他是年少好奇心重并没有多想,就道“你说的那种书据我所知还没有,还是那句话世上药物种类繁多,而人力又是有限,因此现在还没有一种能够囊括所有药材的药物典籍,我这里书籍虽然不少,可很多书记录的内容是相似和重复的,也许在将来会有人能够将诸多药物药材尽数收录在一部书里,我相信那一定会是一部旷世之作,可惜我是没这个能力了。”感叹一声后,他继续道“文安,眼看就要冬天了,你有什么打算?”
文安被他问得一愣,茫然道“打算?打算什么?”
张九龄笑道“我是说天冷了,若是再要下雪,冰天雪地,你还要每天这么来回跑吗?”
文安恍然道“大叔问的是这个呀!下雪天冷也没什么,来回跑没问题,不过就是下雪后药材山货什么的就不好找了,这个比较麻烦。”
张九龄的意思是想让他带着家人来他家里住下,但他没有明说,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,他已经很了解文安了,这少年有主见也有性格也很固执,自尊心很强,虽然是穷苦出身可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受人恩惠,至于施舍也就更不用提了,所以他说话时尽量讲得委婉,也是不想让文安误会。
见文安没明白自己的意思,张九龄也不好多说,就道“要是天气实在不好,你也不必每天都来这里。”
文安满不在乎地道“大叔无需为我担心,我每天跑来跑去只当是锻炼了,要是一天不跑还会觉得浑身难受不舒服。”
张九龄不觉愕然,虽然他已是将文安看做了身怀绝技的异人,可也没料到文安会把每天数百里的奔跑当做寻常的锻炼,这少年的双腿还算是血肉之躯吗?
文安见他神色有异,还有些奇怪,就问“大叔,怎么了?是我说错了什么吗?”
张九龄摇头道“没有,对了小眉最近怎么样?”
文安道“很好啊,没什么事。”说到这里,他又有些紧张,忙问“是她的病会有反复吗?”
见他如此担心徐眉,张九龄心说,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女孩子真是他的亲妹妹呢?能对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如此的好,这孩子的确是至情至性。“小眉的病应该不会有什么反复,但她底子弱,到了寒冬若是受了风寒,多少会有些麻烦,这样吧,一会我开个方子,你去前面抓十副药,从明天开始,每隔十天就给她服一次药,固本培元,扶正驱邪,以防万一。”
文安大喜道“谢谢大叔,我也替小妹谢谢你。”
张九龄已经提笔开方,闻言不觉笑道“谢谢就不必了,医者父母心,我这样也是尽了本分。”写好方子后,他们又闲聊了一会儿,在书房待了近一个时辰文安才告辞离开。
文安拿着方子提着药筐从后院进入九芝堂,见他来了,刚刚闲下来,正坐在柜台后面休息的伙计小张就笑道“你可算出来了?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从后院直接走了呢?”
小张名叫张天宝,是张九龄的一个远房侄子,虽然都姓张,但已非血亲,今年二十四岁,在九芝堂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年。
张天宝虽然机灵,在九芝堂也干了很久,可不论是在学医方面还是药材方面都没有什么天赋,张九龄也曾教过他三年,可他学会的就只是抓药算账,无奈之下,张九龄也只能让他当一个抓药的伙计。
文安来九芝堂次数多了,自然也和张天宝熟络了,每次来有时间二人都会聊几句,张天宝也是能说会道,在他嘴里文安也是知道很多事情。
文安笑道“没和天宝哥聊几句我可不能走。今天生意不错吧?”
张天宝道“还行还行,刚刚忙完,不过掌柜的说过,我们生意好可不是他人之福,所以呢,生意好也不说说生意好,只能说还行还行。就像是门口的那对楹联,那就是掌柜的心声啊!”
那对楹联文安早已记在心里,当初一见时他就是甚为震动,那上联是,但愿世间人无病,下联为,何惜架上药生尘。
这两句话完全表现出了张九龄的医者仁心以及为人处世之道,而文安也很清楚,这两句话绝非只是说着好听,的确是张九龄的心愿。
暗暗感叹一声,文安笑道“那我们就不说生意了,天宝哥,最近镇上有什么新鲜事吗?”
提起这个,张天宝眼睛一亮,招招手示意文安上前,等后者凑到跟前了,他才神神秘秘,低声细气地道“现在镇上都在说掌柜的要收个干儿子了,你知道吗?”
文安一愣道“不知道?大叔没说啊!”
张天宝翻了个白眼,没好气地道“那个干儿子就是你呀!”
文安大惊失色,骇然道“我?不可能!”
见他如此模样,张天宝也有些惊讶,“你不知道吗?掌柜的没对你说过?”
文安使劲摇摇头,断然道“没有,这是谁在胡说八道,大叔什么时候讲过这话了!”
张天宝皱眉道“可大家说得可是有鼻子有眼,就跟真的一样,再说了,我看掌柜的对你那么好,也像是有这个可能啊!你说,要是真有这么回事,你会答应吗?”
虽然店里没外人,大夫都已经休息去了,他还是小声问着。
文安苦笑道“不是我能不能答应,而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,大叔是对我很好,可也没好到要收我当……干儿子的程度呀,天宝哥,这话千万别让大叔知道。”
张天宝却道“万一呢?万一是真的呢?”
文安还是摇头道“没有万一。”话是这样说,可想到张九龄对自己的厚爱和关怀,他也禁不住想,难道大叔真想收我当干儿子吗?他知道张九龄是有收徒为徒的意思,可徒弟是徒弟,干儿子是干儿子,这可是两码事,岂能混为一谈。再说了他也不想当这个徒弟,对于医药他只是兴趣喜好,他可不想为了学医而分心,他的心思一直都在炼气上。
一想到这个文安不免有些心烦,也就不愿再和张天宝说这个,拿出方子道“天宝哥先帮我抓十副药吧。”
张天宝见他脸色不好也就不再多说,拿着方子开始抓药,很快药就抓好了,文安也没了闲聊的兴致,把筐里的草药交给对方后就离开了。
出了九芝堂文安边走边想刚才张天宝说的那些话,想着想着不觉心烦起来,张九龄对他有多好他很清楚,他也知道对方有收他为徒的意思,可他并不想学医,他连徒弟都不想当自然也不会当什么干儿子,可要是张九龄真要当面提出来,他又要怎样拒绝,这是个难题啊!
唉!默默叹气着,他漫无目的在街上走着,不觉间便到了积香居附近,这时忽然就听到有人朗声吟诵道“天若不爱酒,酒星不在天。地若不爱酒,地应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,爱酒不愧天。已闻清比圣,复道浊如贤。贤圣既已饮,何必求神仙。三杯通大道,一斗合自然。但得酒中趣,勿为醒者传。”
那声音清朗低沉而又饱含深情,所谓深情自然是对酒的情意,这诗文安并未听过,但诗句入耳就已了然其中之意,这是诗人对自己好酒爱酒的解释和分辩,以说理的方式来抒情,阐述了他的酒中趣,杯中情,诗是好诗,而这声音也是颇为熟悉,但一时间文安又想不起从何处听过,但心里竟然生起了隐隐恐惧。
心神震动,文安循声望去,很快就找到了吟诗之人,对方就在积香居的二楼,临街靠窗而坐,与他相隔还十来丈之远,此刻那人也含笑看着他,并且正在饮酒,他手里赫然拿着一个血色葫芦,他的酒就在这葫芦中。
见到葫芦即便喝酒之人面孔陌生,文安也禁不住脸色骤变,低低惊呼一声,身躯亦是微微一颤,继而又和对方的目光有了接触,那眼睛那眼神也是极其熟悉的,那目光凝聚宛如实质,与之对视,仿佛在瞬间就已被对方看透看穿,在这双眼睛下文安毫无秘密可言,晶莹剔透,干干净净的就如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。
是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