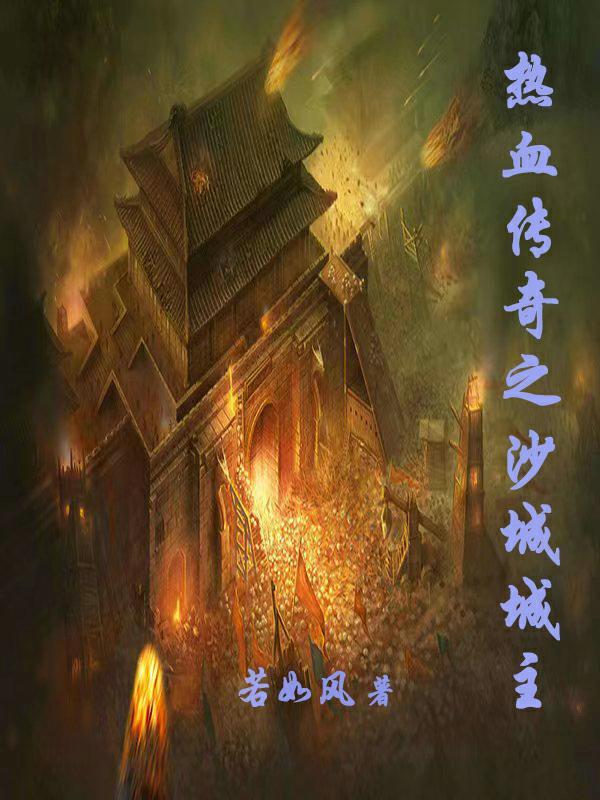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一袖揽凰权 > 第20章 她与众不同(第1页)
第20章 她与众不同(第1页)
“他的失忆什么时候能治好?”黎绿腰盯着面前的太医。
太医白花花的胡子一颤一颤:“这位公子头部受过重伤,少则一年半载,多则……永远都无法恢复记忆。”
“是么?”黎绿腰唇角翘起,极艳的容色此刻更艳。
“殿下恕罪!”太医狠狠跪在了地上,出了骨头撞击地面的清脆声。
“你可知道里头这位公子是谁?”
“这……微臣不识。”太医重重磕头,额头贴在地面上。
“温忠太医是吧?”黎绿腰站了起来,将太医扶起,扶到了椅子上,“温这个姓有些耳熟呢?不知我大皇姐的驸马温岭同你是何关系?”
温忠袖子之中的手一抖:“温岭是微臣的儿子。”
“嗯,本宫知晓。”黎绿腰轻声呢喃,如鬼音入耳,“本宫若不知晓,又怎么会唤你前来呢?”
只这一句,温忠就知道自己一家逃不掉了。
“那本宫再来问你——里头那位公子你可识得?”黎绿腰慢慢踱步,还不忘抬手示意温忠坐着答话,“这次您可得好好回答,本宫可听说,这温家和贺家可是故交呢。”
“微臣……识得。”温忠闭了闭眼,“那是贺家的公子,南齐的大将军贺岁安。”
“本宫听说你可是看着贺家公子长大的,所以……可务必要治好他。”黎绿腰微笑道。
“微臣定竭尽全力。”
“您且好好治,治好了就能走了,若是治不好……”黎青鸾话语顿了顿,“您应该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。”
“微臣遵命。“温忠再度跪了下去,俯。
此时,贺子行疾步走来,附到黎绿腰耳边说了几句话,黎绿腰站起身来,还不忘对贺子行道:“看着点温太医,温太医年龄大了,经不起折腾。”
“是!”贺子行躬身,目送黎绿腰离开,走到温忠面前想搀起他,却被温忠拂开手。
贺子行脸色不变,只听温忠道:“我不知你与岁安有何恩怨,竟害他至此。”
贺子行却不答,只淡淡道:“您还是治病吧,多余的话您说了也没用。”
温忠满目沉痛,有些佝偻的身躯慢慢走向室内。
贺子行却是紧握手指,指尖泛白。
与此同时,在通往南齐的官道之上,哒哒的马蹄声如雷点落在天幕上,在寂静的夜里震耳欲聋。
黎青鸾利落一勒缰绳,停在了一片林子之前,她趁一行人在客栈落脚之时,找了能锻炼身手的地方。
她将马拴在一边,起身下马,不过短短几日,她的大腿已经被马鞍磨伤了,已经沁出了血,但她无法停歇,血海深仇在前,她一刻也不能停。
黎青鸾拿着从皇帝派来的杀手那儿抢来的匕,这匕削铁如泥,倒是个好东西,她要把这个好东西在她手中挥到极致。
匕划过夜空的声音如同野兽出的低鸣,让人心生畏惧。黎青鸾闭着眼睛,想着自己过去学的一招一式,一点点调整动作,尽量达到与过去一样快准狠的效果。
“这女人……真是粗鲁啊……”看着黎青鸾逐渐迅的动作,离底蹲在树枝上,悄悄俯视着她。
“你来这儿干什么?看上她了?”离扇慢悠悠扇着扇子。
“我看上她?”离底满目不可思议,“这么粗鲁的女人!要不是主子让我来看看她做什么,我才懒得来!”
离扇悠然笑了笑:“没看上她最好,总而言之,离她远点。”
“为什么?”离底眉毛拧在一起。
离扇同情地看了看缺根筋儿的离底,却是不准备开这个口,毕竟照离底的性子,他说了离底也不会信的。
就在这一刹那,锃亮的雪色直冲他们而来,离扇动作快,率先跳下树,离底却还没回过神,反应慢了一拍,被削断了一根头,匕却是深深插进了树干之中,只留把柄在外头。
被削断的头慢慢悠悠落了下来,离底蹲下地上,捧着他的一缕头眼泪汪汪:“我的头啊……”
黑靴自他跟前迈过,离底抬头去看,只见月色之下浑身煞气的女子拔出了树干之中的匕,垂看他:“你们鬼鬼祟祟干什么呢?”
离扇打开扇子,笑说:“真是好巧,我们来赏一赏这林子之中的好景色。”
黎青鸾扫视了一下漆黑夜色之中显得鬼气森森的树林,愣是没看出来半点好看。不过她也懒得去想他们的目的。她一捋袖口:“来都来了,跟我比试比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