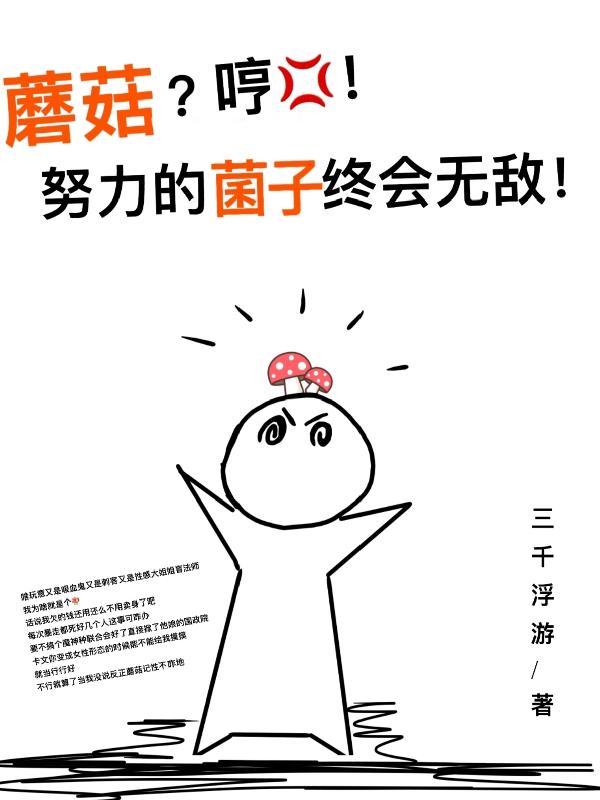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家族遗传精神病n虐 > 第四章事不过三父子同穴电击(第3页)
第四章事不过三父子同穴电击(第3页)
他随母姓,早死的爸是德国人,遗传了深蓝色的眼睛和稍显深邃的面孔,骨架大,练过各种散打、武术,举孟惠织跟举娃娃似的。
“放我走吧……”孟惠织声音虚弱,头搭在他的肩膀上,无力的晃动,现在时间肯定过了,不敢想象回家之后会怎么样。
她缴着肚子,希望陆渊赶紧射出来。
直到地上的光斑消失,陆渊才射出来,他放下孟惠织,掏出一张卡扔到地上:“密码是尾号六位。”
“走了。”
两个人整理好衣服,一前一后离开。
大门关上,孟惠织长出一口气,捡起银行卡,穿上皱巴巴的校服,忍着身上的不适,跑到外面搭车,一看手机,已经7:42了,有2个未接电话,内心一阵绝望。
跑回家,她打开门,放下书包,跪在玄关。
一个穿着贴身的红黑条纹西装,气质成熟,外表一丝不苟的中年男性走下楼梯,挂掉电话:“惠织,为什么又回来晚了?”
孟惠织头埋的很低,一言不。
男人坐到沙上,打开电视,调到动物世界的频道:“过来。”
孟惠织膝行到他旁边,屁股压着脚趾,头虚虚的放在他的膝盖上,像只小动物。
两根手指掐着她的脸颊,几乎把她的脸皮揪下来。
“你准备接受哪种惩罚,扇脸,打手,还是打屁股。”
孟惠织抖着手解他的皮带“父亲,我给你舔……”
男人没有阻拦,一双铅灰的眼睛看着电视。
“春天到了,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。”配音解说草原上狮群的交配,雄狮的阴茎长着倒刺,倒刺能刮出其它雄狮的精液,并且困住母狮。
孟惠织握着硕大的、沉甸甸的性器,心一横,一口吞下去,捅进喉咙,眼神飘到父亲的脸上,希望能看到他哪怕一点点高兴的样子。
男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,完全看不出他的女儿给他口交。
大手按住她的后脑勺,往下施力,孟惠织甚至听到了颈骨“咔哧、咔哧”的声音,喉部受到刺激,阵阵反胃,眼泪鼻涕不受控制的流出来。
她不敢有丝毫挣扎,尽力的放松,把这个东西全吃下去,鼻梁陷入黑丛。
大掌握着她的后脑前后摇晃,直到喉咙泛出血腥味,下巴快要脱臼,孟景庭才松开手。
孟惠织一滴不漏的吞下去。
“扇脸,打手,还是打屁股。”
“呃、喝——”孟惠织想求饶,才现说不出话,她的嗓子磨坏了。
孟蝉封进屋,看见父女二人在客厅,问道:“她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
“刚刚。”
两双相似眼睛的对视,迅错开。
孟蝉封脱下墨绿色风衣,摘掉百达翠丽手表,甩到茶几:“才吃过教训,转眼就忘了,你是在故意惹我生气吗。” 孟惠织双手撑着木地板,浑身颤栗,虽然穿着衣服,却觉得处在寒冬十月,浑身泛起鸡皮疙瘩,恐惧在他的视线里节节攀升。
“啊!”
恐惧爆了,手特别用力的拉着她的头,几乎要扯掉头皮,身体摔到地板上,她下意识的卷缩,捂住柔软的腹部。
身上又添了几枚脚印,孟惠织挨打习惯了,还能忍受,可孟蝉封从茶几抽屉掏出来的东西,她不太能忍受。
看上去像情趣用品,但都经过改造,其中手铐是从五金店买。
孟蝉封拿着两副手铐,咔哒两声,将孟惠织的左脚和左手,右脚和右手铐在一起,让她只能保持一幅双腿大开,弓着背部的姿势。
他的脚趾踩着孟惠织的阴唇,那两片可怜巴巴的肉搭在那,因为长期过度使用,颜色很深,逼肿的跟馒头似的,颜色艳红。
“喝…哥……对……求……”每说一个字,喉咙都会冒出一股锈味。
“啊——”孟蝉封狠狠地朝她的逼里踢了一脚,脚拇指嵌进去,孟惠织想捂住,但是手被金属镣铐勒着,嵌出一圈红痕。
裤腰带抽出来,令人窒息的破空声之后,与皮肉接触,出清脆的声响。
“啊啊啊啊咳咳——”孟惠织在地上翻滚,皮带比藤条长,打人更疼,打过的地方泛出红痕,过不了多久,就会变成一条带深紫斑点的淤痕。
“呜呜呜咳咳……呜啊——”
孟蝉封越打越兴奋,下体高高翘起,扔下皮带,就着干燥的穴插进去。
施暴欲和性欲,孟惠织都能帮他解决,这就是他的妹妹在这个家最大的用处。
“不呜——咿呀——”孟惠织出令人心惊的哀嚎,完全出尺寸的肉棒破开穴肉,狠狠的撞在尽头。
好痛,好痛……她大张着嘴,泪流满面,她的逼早就烂了,日复一日的折磨,让伤口迟迟不能愈合,每夜靠止痛药入眠,性器侵入她的阴道,粗糙的表面似无数的小刀,割刮敏感的神经,仿佛含着烧红的铁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