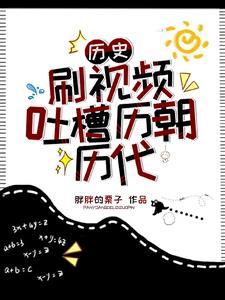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谍战:我当恶霸能爆奖励! > 第316章 这是驻巡所还是忠义堂啊(第1页)
第316章 这是驻巡所还是忠义堂啊(第1页)
王小手开门走到外边,只见一个穿着亮蓝大褂,头梳的苍蝇都站不住脚的年轻人掐着腰趾高气昂,这人白净面皮,眼窝深陷,两颊潮红,一看就是沉迷酒色的人。
按理说这种人一般不会到二荤铺来,但王小手一看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
要是搁平时,王小手非得跟他掰扯掰扯,现在林泽在屋里面,王小手不想扰了林爷吃饭的好兴致,当下一拱手,“我当是谁呢,原来是王少爷,您不去全聚德、春华楼唔得,怎么上这儿来了?”
这年轻人名叫王康安,原本只是个外城的破落户,天天给人帮闲过日子,后来那些个遗老遗少自己兜里也没两个子儿了,自然养不起什么帮闲,而且这个王康安在帮闲群体里也是那种等级最低的。
高级的帮闲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放鹰斗狗样样全行,可这个王康安大字都不识一箩筐,别说琴棋书画了,倒是有一点,就是能票上几句戏,擅长的还是旦角,所以有一段时间倒是有几个口味儿独特的遗老遗少捧过他。
因为手里没钱,所以以前的王康安吃顿二荤铺也算是开了荤了,但现在可不一样了,现在他来吃二荤铺,那叫怀念过去在街面上的日子,改不了这口儿!
人家现在趁起来了,他有个本家大爷,是治委会内务总署调查一处的处长,叫王光远,这王光远年近五十,还没有儿子,着急之下,就要在本家里面过继一个。
王康安长得还算不错,又能说会道,这王光远就选中了他。
这不,王少爷现在走路都是一摇三晃的,用他的话来说,就是他爹是内务总署的处长,一般的人物,还真不放在他的眼里!
王康安见了王小手,脸色略微缓和了一点,敷衍的一拱手,“原来是本家啊,你给说说,可气不可气!我王康安现在是什么身份?就跟你说的那样,我就算到了全聚德、春华楼这样的大馆子,他们掌柜的也得尊着敬着,这董胖子倒好,我今天就想这一口了,到他这来,他跟我说什么今天不做生意,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!”
王小手心里呸了一声,滚你娘的,谁跟你是本家,你一个兔爷,在我面前放什么份,还春华楼掌柜的也得尊着敬着,你真听不出来好赖话了是吧!
当下也不客气了,“王少爷,今天这里边有贵客,您改日再来吧。”
本来王康安觉得王小手在这,能给自己几分面子,毕竟他只是个小小的巡长,自己那便宜老爹可是治委会的官儿,差着不知道多少级呢!
没想到王小手竟然一点都不客气,开口就要撵人。
这穷人乍富和小人得势,最怕别人看不起他,一遇到这种事儿,八成都得上头。
王康安这就上头了,那种无赖劲儿又使了出来,“还贵客?这破铺子能有什么贵客,是拉车的还是担担儿的,我说王小手,你一个以前街上的三只手,能有什么贵客?哈哈,我看怕不是什么堂子里的龟公,来跟你”
王小手一听,面色大变,绝不能让他再说下去!
刚抬手要打,只见从屋里窜出一个身影,飞起一脚,直接把王康安踹出去三米远。
上前两步,踩住王康安的脑袋,顺手就把枪掏出来上了膛。
来的不是别人,正是钮三儿。
王康安都傻了,这一脚踹的他气血翻涌,几乎要吐血,可抬头就看见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自己,愣是没敢说话。
钮三儿看都不看他,反而扭头看向王小手,“小手哥,主辱臣死啊!”
王小手又气又急,都红温了。
这年头的人对士为知己者死这件事儿看的太重了。
王小手、钮三儿这些人以前都是最底层的人,是林泽给他们铺了一条往上爬的路。
就拿王小手来说,以前是人人喊打,现在辖区里谁不尊称一声王巡长?
可今天就在辖区里头,竟然有瞎了心的敢骂林爷,林爷可就在屋里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