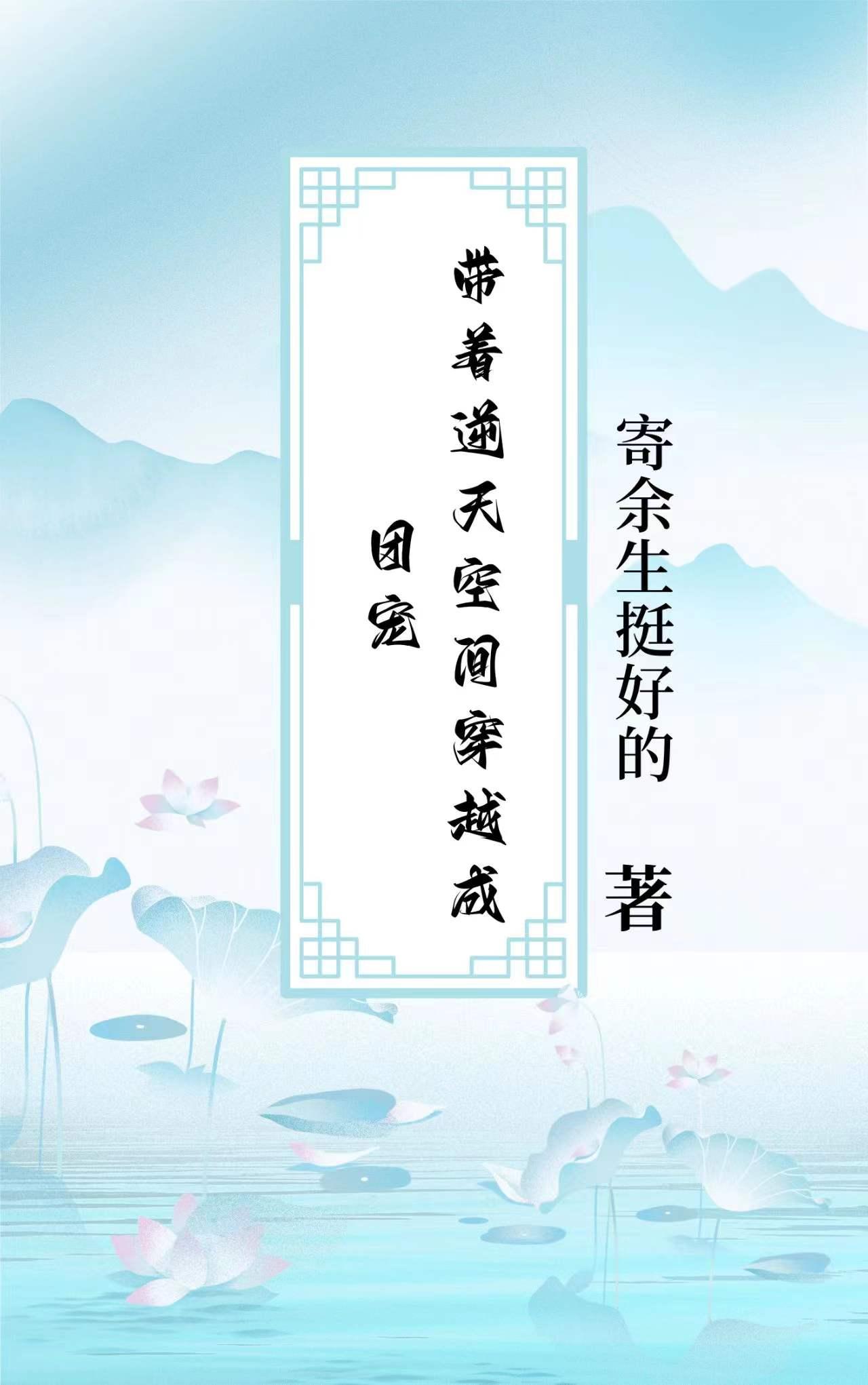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权倾天下政斗古言 > 81突然升官(第1页)
81突然升官(第1页)
温湛把皇帝皇后的话都带给了龚肃羽:皇帝死活不放人,别说你辞官,哪怕你揭竿而起或是逼他禅位也没用,要美人不要江山;而皇后则完全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向着皇帝求亲爹太平点,别老凶巴巴地折腾女婿。
贴心小棉袄温大人说得再委婉,意思就这个意思,龚阁老听到耳朵里立时化为熊熊怒火,在胸膛猛烧爆燃,“叮”地一声放下手中茶盏,差点砸了宫里的瓷杯。
“堂堂一国之君,竟沉迷儿女私情至此,置天下社稷于不顾,百年之后有何颜面去见传位于他的先皇!”
温湛忍了又忍,好不容易憋住没有当场吐槽双标老头,要论沉迷儿女私情,睡自己亲弟弟的先皇永嘉帝与你这个娶自己亲儿媳的辅,那都是当仁不让的前辈啊,皇上比你们差远了。
总之辅夫妇想从宫里捞女儿的谋划功亏一篑,反倒让那对苦命鸳鸯心意相通,更添患难深情。
皇后借着照料病中皇帝的籍口留在乾清宫,朝夕相处,日夜缱绻。昭仁帝不可操劳,司礼监送来的奏疏本该由太监念给皇帝听,结果这活也被小皇后接了过去,坐在恪桓腿上或是靠在他怀中,嗲着嗓子慢条斯理逐字逐句地朗读。
她不懂政务,年纪小又生性好奇,读个奏疏一大堆问题,恪桓非但不嫌烦,耐心一一解答,还时常问她意见,或是一起抱怨奏疏里废话多、事情难办,倒比他一人闷头批阅要开心得多。
“为什么六安受灾后迁去通州养的马匹非但不产驹,还死了八九成?是水土不服吗?买补之后数月,又复如前,瘦死赔买,致马户倾家荡产,鬻及男女,怎会如此……”
自小养尊处优的皇后第一次看到天下小民的艰难,为了应对官府岁征,或是额外科索,倾家卖子者比比皆是,读完浙江道御史上报的奏疏,思及百姓卖儿卖女妻亡子散的惨状,不由沧然泪下。
昭仁帝点点头,亦觉沉痛,“许是两地所生草质不同,亦或是气候,内阁票拟怎么说?”
龚纾再看票拟,是亲爹的字,笔锋大气庄严,心里生出暖意,觉得父亲一定会有好办法解决。
她仔细阅读,而后概括转述皇帝:“内阁说事先不行勘察试养,就把六安的马迁去通州,强行摊派马户,至民不聊生,要把六安抚按官员贬黜问罪,此为其一。
令御马监尽快派擅养马匹之人南下另寻适养之地,免去通州马户岁征,若有懂马之人,免去当地宗室及官派苛役,记录在册,待牧马之地选定,则迁至该地协同教授当地官员及马户饲马,此其二。
宗藩旁支繁衍如林,子孙所占之地愈广,与国争与民争,西北疆域太仆寺官牧之地所剩无几,以至于朝廷用马八成出于强征马户,非长久计,宜改制,此其三。”
说前两条时皇帝还频频颔,听到最后一条却讶然蹙眉,沉思良久。
“刘安,替朕传旨内阁,授兵部侍郎温湛东阁大学士,加封太子少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