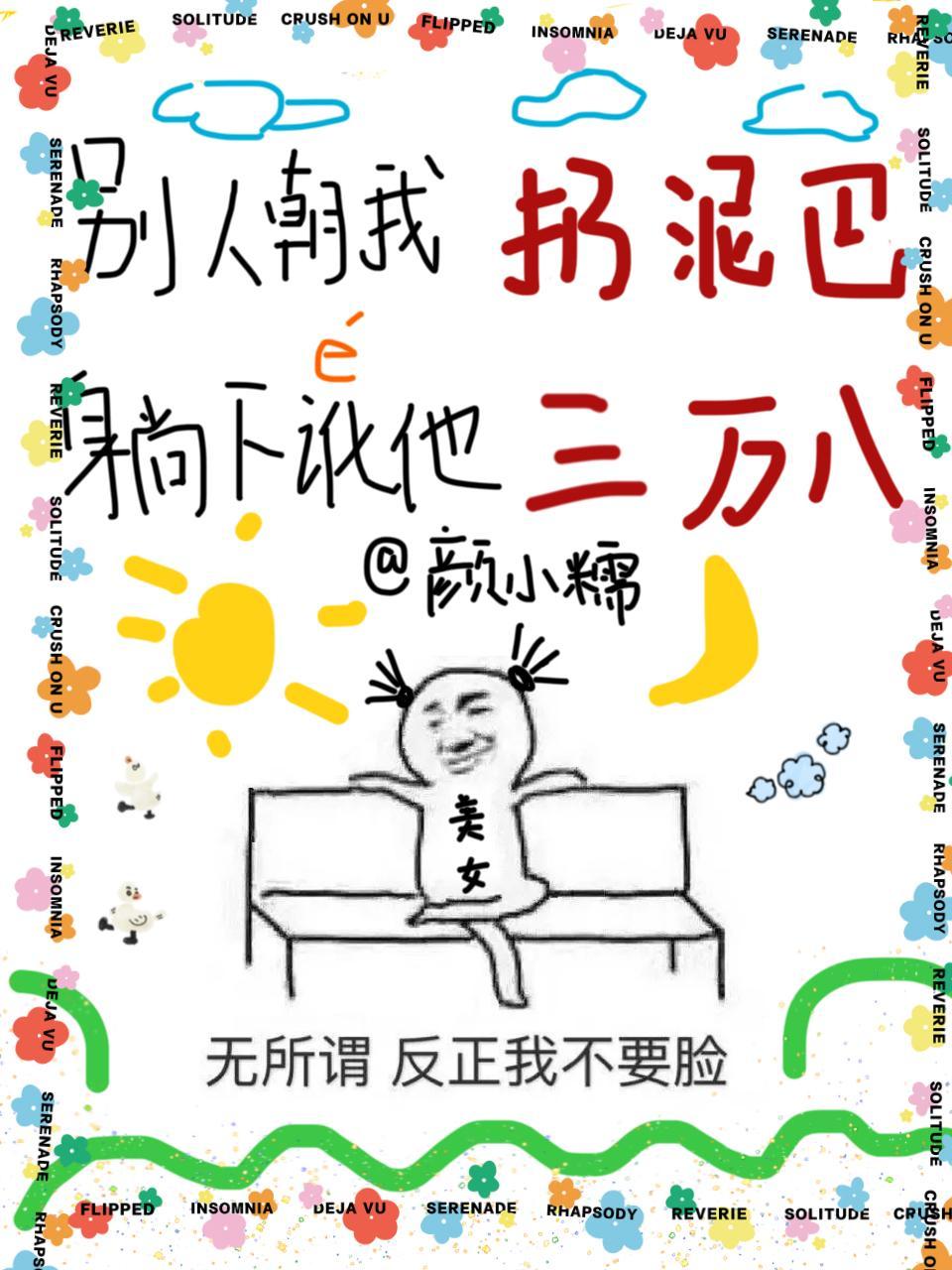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纾春 > 第61章 她的中原名(第1页)
第61章 她的中原名(第1页)
崔礼礼循声看去。
是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。
那小姑娘一看就是木蛮人,十五六岁光景,穿着宝蓝色的木蛮裙,缀着百十来个丁零当啷的银铃铛。梳着满头的小辫子,眼眸又圆又亮,唇角微微翘着,极其娇憨俏皮。
那小姑娘对崔礼礼友善地笑了笑,又上前一步,对人牙子说:“你打坏了,还怎么卖?”
这小姑娘的中原口音有些生涩。人牙子眼珠子一转,将鞭子插在腰后,一把拽起番奴,拍拍番奴身上的土,腆着脸道:“您可要买?您看,都好着呢。”
小姑娘上了台子,围着番奴们转了好几圈,捏胳膊,揉胸口,还捏开嘴看了牙口,掐了掐腰,最后拍拍番奴的屁股,拉出三四个来:“则几个,都不错。”
人牙子脸上都笑开了花道:“十两银子一个。一起买,算您八两一个。”
“我买不起。”小姑娘拍拍手,跳下台。
看她那一身银铃铛,扯下一串来,就够了。怎么会买不起,根本就是不想买,上台来捣乱的。
“你不买看什么看?!”人牙子龇着牙,抽出鞭子来。
“她想买,我帮她看的。”那小姑娘指了指崔礼礼。
樊城人站在后面,笑着起哄:“你跟人牙子是一伙的吧!想讹人家。”
“不,”小姑娘摆摆手,又看向崔礼礼,“我跟她一起的。”
她什么时候认识这个小姑娘了?崔礼礼一楞,怎么樊城人看热闹没事,自己看个热闹,又摊上人,又摊上事儿了。
那小姑娘走向崔礼礼,一步一脚都伴随着银铃的清脆声,她眉眼亮闪闪的,操着不纯熟的中原话说道:
“这几个我都看了,胳膊和腿,有劲!腰,有劲!牙都齐!屁股也够翘!”说着她的手还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弧,“你买吧,不亏。”
这一番话说下来,整个人群都炸开了锅。
都说番邦女子开化,可这姑娘是木蛮人,木蛮人是番邦中的异类。木蛮人的女人是见不得光的,他们的教义之中,女人是罪恶肮脏的之源,若被阳光照耀,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
一个女子,从出生就只能待在家中,万不得已要出门时,必需从头到脚蒙上白布,布上会绣着父族的姓氏。
等到女子嫁了人,布上就会绣着丈夫的名字。若丈夫去世,就会将白布换作黑布,布上改绣儿子的姓名。
这样的番族,怎么会出现小姑娘这样的人。
番奴再贱也是男子,当街摸来摸去还品头论臀,木蛮人知道了,会剥掉她的衣裳,丢进深山里,自生自灭吧。
“你买吧,放九村楼,生意好。”木蛮小姑娘似乎还挺真诚。
九村楼?是九春楼吧。看来是真认识自己。也不知道她什么来历,崔礼礼不敢随便回应,只摇了摇头:“我是想买,但我没有钱,也带不走。”
那小姑娘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,有些失望:“那下次,下次,我帮你看。”
人牙子一听不乐意了,怎么又不要了。那怎么行?提着鞭子就跳下台来:“我的人你们就白摸了?给钱!”
小姑娘拿起身上的一串银铃铛,放到人牙子手里:“够不够?”
人牙子掂了掂,这一串少说也有五两银子,旋即笑着道:“够,够!”手正要合上,不料到手的铃铛飞走了。
“你摸了银子,我摸了人,扯平了。”
围观的樊城人笑得前仰后合的。这要是在青楼,早就被人打出去了吧。可番奴又不是青楼的姑娘,自是不能这样算的。
眼看着人牙子恼羞成怒,崔礼礼不想节外生枝,抛了一点碎银子过去,对木蛮姑娘道:“这位姑娘,还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两个小姑娘找了一处茶肆。崔礼礼要了两碗热茶。木蛮姑娘喝了一口,道:“还是不如我们那儿的马奶茶好喝。”
“你认识我。”崔礼礼审视着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