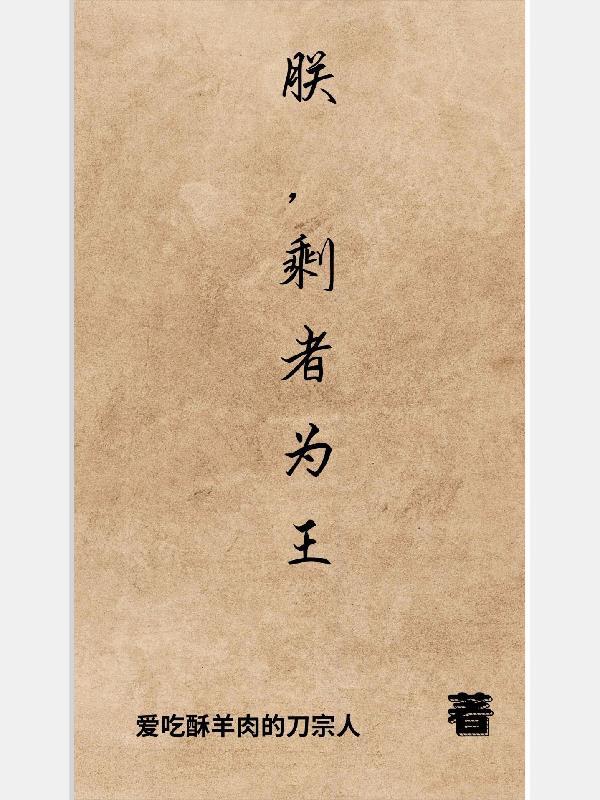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七零宠婚,硬汉兵王被小娇妻拿捏了 > 第104章 最后的愿望是回家(第1页)
第104章 最后的愿望是回家(第1页)
“金昌?多大年纪?”魏定邦突然出声问道。
男子哭得太厉害了,声音断断续续的:“金昌大哥看着四五十岁了。”
魏定邦松了口气,老班长只比他大两岁,可能只是个名字相同的犯人。
老班长是立过战功的,是残退的,是个忠贞坚定勇敢的军人,绝对不可能做违法乱纪的事,更别说是犯罪被送入农场。
他身手也不错,哪怕只剩下一只胳膊了,可等闲三两个人也别想近他的身。
男子口中那个被要打得满地乱爬的可怜人肯定不是老班长。
“金昌大哥才三十八啊,进农场才三年,生生被熬得老了十几岁。
一直是他护着我们这些新进去的生瓜蛋子。
可那些人太阴险了,在他的吃食里下安眠药……
直接生生折断了他的腿……
十几个人围着他用胳膊粗的棍子砸……
整整打了一个多小时……
他腿上的骨头都被砸零碎了,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,我也要背着他逃的啊,可他把我从墙上推了下来,他说他不能拖累我,让我快走。
我只能边跑边回头望,看着他被那些畜生像拖死狗一样拖回了农场的狼狗窝……
那些狼狗,那些狼狗,可是吃……吃生肉长大的……比野狼还要凶残……”
“你说什么?”独臂,三十八岁,好护短,还叫金昌,这么多对应的信息,那人一定是老班长没跑了。
魏定邦目眦俱裂,用力捏着男子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,咬牙切齿地问道:“你说他被人放了药药倒了,十几个人围着打,打了一个多小时,骨头全砸碎了,还被扔进了狼狗窝里?”
“是,是啊……”
“多久了?!”
“啊?”
“我问你,这事生多久了?”
“两,两天……”
两天!
一个手脚骨头都被砸碎,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,能在凶性被完全激出来的狼狗窝里存活下来的希望极其渺茫。
魏定邦双手紧紧握住,胸脯剧烈地起伏着,脖子上的经脉抖抖地立起来,面色冷厉,青筋从脖子一直凸到耳朵后。
“立刻带我去农场!”魏定邦的声音一个一个字从牙齿缝里迸裂出来,带着某种震慑人心的力量。
男子浑身颤栗,强撑着摇头道:“我,我脚软,走,走不动了。”
他从农场逃了出来,两天两夜都不敢停歇才走到了红兴医院。
他饿得实在太难受了,才偷溜进医院想找点东西吃。
可是现在的粮食也都金贵,病人们吃饭每一粒米都刮着吃进了自己肚子里,碗干净得像被洗过似的。
他在放潲水桶的地方守着,也没找到什么能吃的。
他来尿尿,看到那黄汤从自己身体里流了出去,都一阵阵的心疼,有一刻,他还像疯了似的想过,要是实在不行了,喝尿也要活下去。
魏定邦把男子拎了起来,像抓着小鸡似的提到了楼顶上,指着水塔后的角落让他好生待着。
下楼借了笔和纸,又把剩下的那个煮鸡蛋拿上,重新上了楼顶。
水塔后却没人了。
1o2。
魏定邦拧着眉头抿着唇往楼顶门那边走。
笔被他的手指捏得咯滋滋的响。
等他走了之后,水塔顶上才慢慢地探出一颗人头。
他迟疑了片刻,慢慢地从水塔上梭了下来,瘫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