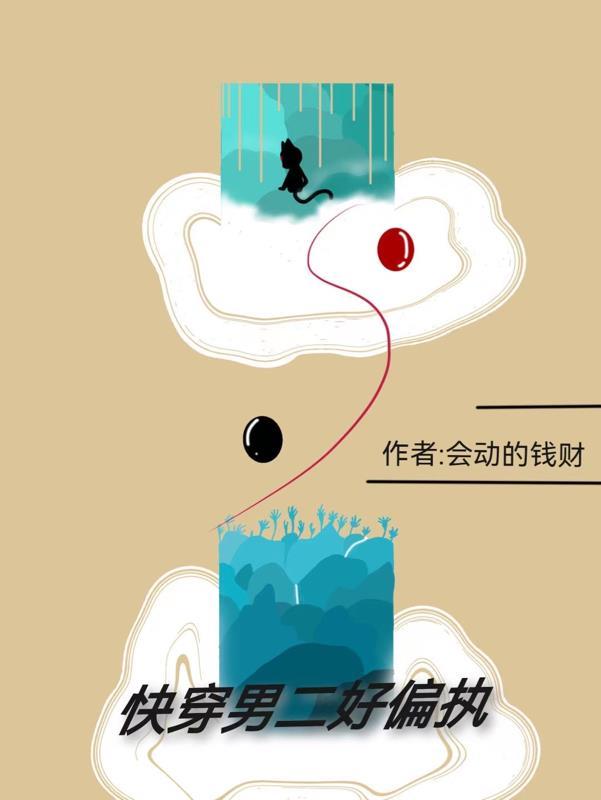乐视小说>我只想被我拯救过的反派抛弃 > 第 55 章 烧灯续昼五(第3页)
第 55 章 烧灯续昼五(第3页)
姜重山问:“照你这么说,你不认击杀樊鹰是你的功劳,那又是谁的?”
“自然是您的。”
姜重山四下看看。
他真想找个什么趁手的东西,揍他两下,可目光所及,不是桌椅板凳,就是刀枪棍棒,他挑了一圈,只得作罢。
“你要把我气死是吧?”
宴云笺俊颜苍白,漆黑长眉微挑舒展一笑,微微抬手:“义父,便当是阿笺求您。”
姜重山一时无话。
这个孩子,从来没有求过自己任何事,第一次请求竟是为此。
“就算你这么说,我也不可能毫无负担将此事安到自己头上,那我成什么了。”
说来真是啼笑皆非,击杀樊鹰此等头功,他们父子竟推来推去,无人肯认。
姜重山望着宴云笺,明白他心意
坚决,绝不更改,就算强加给他,他也不会要。
他摆摆手:“罢了罢了。此事先不急着谈,我这儿还有话问你呢。”
姜重山抿一抿唇,目光上下扫过宴云笺,“方才你刚清醒时干的好事,该不会就当是忘了吧?”
宴云笺眉目一僵。
“嗯?说话。”
“孩儿……没忘。”
忘是不可能忘的,算下来,他有大半年没见阿眠了。思念不仅没有减淡,反而越积越深重压心头。
老天也算厚待他,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他时不时便会梦见阿眠。
是他放肆,在梦中,竟一次次松懈了自制力——可他绝没做过分之举,只是梦境黑甜,他有时会忍不住牵阿眠的手,抚一下她脸颊,除此之外,再无旁的了。
方才……
宴云笺低头,无话可说。
他当是梦。阿眠离自己这样近,还握着自己的手,他浑浑噩噩,竟下意识触碰了她。
宴云笺所有神色都被姜重山尽收眼底:“阿笺,从你进家门的第一日起我便说过,你此后就是阿眠的亲哥哥。我原本以为你听得进去,也收了心思,却不曾想你只是将心思瞒的这般好,连我都被骗了过去。”
宴云笺双手不自觉揪紧身上棉被,看一眼姜重山,缓缓起身,想下地跪下。
“哎——别动。”
姜重山拦了他:“一身的伤,乱动什么?”
宴云笺薄唇微动,声如蚊蚋:“义父,我……”
“说这些并不是怪你,阿笺,你心思重,竟把对阿眠的情意隐藏的这样好,若非方才神思混沌,只怕你要隐瞒一辈子也不说,是与不是?”
宴云笺垂不语,眉宇间泄出几分惭愧。
姜重山温声:“你不必自责,为父只是想把话与你挑明了讲。”
“阿笺,你是个很好很好的孩子,我喜欢,也欣赏。你的身份,虽然特殊,但在我眼中,也并不算什么。那些都是前尘往事,根本不足以成为你的拖累,或是牵绊你的人生。若抛开一切不论,单从匹配二字而言,你与我的阿眠很相配。”
什么?
宴云笺听的愣住,缓缓抬头望着姜重山。
这转折与他想象的不一样。
姜重山眼中落了些笑意。
阿笺一向运筹帷幄,他还从没在他那双聪敏的眼眸中看到如此呆愣的模样。
姜重山笑过后,又正色:“阿眠她……我只希望有个能护得住她的人,待她一生一世,不变初心。所以,说实话,在世间男儿的人选中,我最中意你。”
他不知往后还会不会遇见对阿眠如此深情的男子,只是方才宴云笺睁眼时那几可触碰的浓烈情感,让他这个局外人都险些灼伤。
“但是阿笺,义父也要与你说明一点,如今阿眠才刚刚及笄,我定要多留她几年在身边。再者,她还没生出任何绮思,看你,与看阿峥并无不同,所以此事最终也要看阿眠自己的意愿。”
宴云笺一直都听的呆愣,直到这一句才勉强找回些思绪:“这是自然,对阿眠,当然半分也勉强不得。”
姜重山微微笑了下:“你能这样想,义父很高兴。不过,等开春你便要及冠,也该娶妻,若是一昧等阿眠,义父也怕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我并不忍心,你要怎么选择,都是你的自由。”
宴云笺忙摇头:“不,怎会是耽误。”
“义父,我……”这话说来,实在有些难以启齿,他从未想过此生竟还能有如此剖白的机会。
但还是要说。宴云笺声音低,却说的清楚坚定,“我心悦阿眠,本自知痴心妄想,早已做好打算,此生不娶。若是……”
若是他还有半分机会……
他微微闭目,心绪起伏,再给他五年,不,三年,他一定了却肩负责任,那时若义父还同意将阿眠嫁给他,阿眠也愿意的话,他必定将她如珠如宝捧于掌心,疼宠一生。
他未竟之语,姜重山都明白:“若你心意如此,义父便不再劝你什么,等阿眠再长大一点,她欢喜这门婚事,我便将她嫁给你。”!